阿公躺在床上睡,心裡也在默默算,他還能醒來幾次
阿公躺在床上睡,心裡也在默默算,他還能醒來幾次
一場關於時間、記憶與告別的漫長獨白
窗外的光線又移動了幾吋。我知道,因為那道光剛好從衣櫃的把手,慢慢爬到了牆上的那幅舊日曆邊緣。這是下午三點的光景,帶著一點點灰塵飛舞的金黃色,但我沒有力氣轉頭去確認。
我躺在這裡,身體沈重得像是一袋吸飽了水的舊棉花。呼吸是唯一證明我還活著的節奏,那是一種甚至連我自己都覺得吵雜的聲音——嘶...呼...嘶...呼...,像是一台缺乏潤滑油的老風箱,在空蕩的房間裡拉扯著。
「阿公,喝點水好不好?」
耳邊傳來媳婦的聲音,很輕,像是怕驚擾了什麼易碎的東西。我費力地眨了眨眼,那是我唯一能做的回應。沾了水的棉花棒塗在乾裂的嘴唇上,那一點點涼意,順著神經傳遞到大腦,告訴我:這是一次。我又醒來了一次。
第一章:加法與減法的算術題
人老了,就會變成數學家。
年輕的時候,我們算的是加法。算還有幾天發薪水,算存摺裡多了幾個零,算還有幾年孩子才會長大,算還要拚多少業績才能換那台新車。那時候的時間是無限的資源,我們揮霍它,像是用不完的井水。
但現在,我算的是減法。
醫生說我的心臟像是跑了二十萬公里的引擎,隨時可能會熄火。兒子問醫生還有多久,醫生說得很含蓄,說要看這幾天的狀況。他們以為我睡著了,以為我聽不見。其實聽覺是人最後退化的感官,我聽得清清楚楚,甚至聽見了兒子壓抑在喉嚨裡的哽咽聲。
於是從那天起,我就開始算。
我睡著了,然後醒來,這是一次。
我又睡著了,再次睜開眼看到天花板的水漬,這是兩次。
午睡醒來聞到廚房煮稀飯的味道,這是三次。
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。因為每一次閉上眼睛,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最後一次謝幕。黑暗像是一張溫柔的大網,會讓人感到無比的舒適、放鬆,那種誘惑力是巨大的。只要我不掙扎,只要我順著那股黑暗滑落下去,一切疼痛都會消失,背上那些褥瘡的刺痛、胸口那種被大石壓住的悶絕,統統都會不見。
但我還是掙扎著醒來了。為什麼?
心裡有個聲音在說:「還不是時候。」或是,「我想再看一眼那個小孫女。」
昨天我醒來了四次。今天到現在,這是第三次。數字越來越少,間隔越來越長。夢境與現實的界線開始模糊。剛才我以為我看見了阿秀,我的太太,她穿著我們結婚那天的紅色旗袍,站在門口對我笑。但我一眨眼,她變成了衣架上掛著的一件舊外套。
阿秀走了十年了。我在心裡默默對她說:「別急,讓我再算幾次。再讓我贏過閻羅王幾次。」
第二章:天花板上的電影院
躺在床上的人,全世界就只剩下天花板。
我的天花板是白色的,但在角落有一塊因為樓上漏水而留下的黃色水漬。那塊水漬形狀很奇怪,有時候看像是一隻奔跑的狗,有時候看像是一張哭泣的臉。
在這個小小的方框裡,我開始播放我的一生。
第一幕是泥土的味道。
那是民國五十年左右吧?那時候我還是一尾活龍。家裡的田地剛收成,我光著腳踩在還留有太陽餘溫的田埂上。那種腳踏實地的感覺,現在想起來竟然奢侈得讓人想哭。我記得那天阿秀提著鐵壺走過來,裡面裝著冰涼的冬瓜茶。她那時候還沒有白頭髮,笑起來眼角只有快樂的細紋,沒有歲月的刀痕。
我想伸手去接那壺茶,手一抬,卻發現自己的手背上插著點滴針管,皮膚皺得像是乾枯的樹皮,滿是老人斑。
幻影消失了。
第二幕是那台摩托車的引擎聲。
兒子剛出生的時候,家裡窮。我騎著那台二手的偉士牌,後面載著用塑膠繩綑綁得像座山的貨物,在台北的巷弄裡穿梭送貨。雨天是最苦的,雨衣總是破的,雨水順著脖子流進背脊,冷得刺骨。但我心裡是熱的,我想著回家能抱抱那個軟綿綿的小傢伙。
現在那個軟綿綿的小傢伙,已經變成了坐在床邊椅子上,眉頭深鎖的中年人。他的鬢角也白了。
我看著他,心裡突然湧起一陣愧疚。孩子,把你養大,看著你變老,現在還要你看著我腐朽。這就是父子一場的宿命嗎?看著你疲憊的臉,我真想爬起來拍拍你的肩膀,說聲「辛苦了」,但我連抬起手指的力氣都湊不齊。
所以我只能閉上眼。算了,這一次不算醒來,這一次算我偷看的。
第三章:身體的叛變
年輕人永遠無法理解,身體變成一座監獄是什麼感覺。
你們覺得想翻身就翻身,想抓癢就抓癢,那是天經地義的事。但對於躺在這裡的我來說,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場巨大的工程。
我的背很癢,可能又有哪裡破皮了。那個訊號從背部傳到大腦,大腦下達指令給右手,但是右手拒絕執行。它沈重地癱在那裡,像是別人的手。我試著用盡全身的意志力去挪動它,結果只換來指尖微微的顫抖。
挫折感比疼痛更折磨人。
曾經這雙手,可以單手扛起五十斤的米袋;曾經這雙腳,可以騎腳踏車環島。現在它們都背叛了我,罷工了,只剩下心臟還在勉強維持著基本的運作。
我聽到看護阿姨在跟媳婦說話:「阿公這兩天尿布換得很勤,消化好像不太好。」
尊嚴。這是我默默算著還能醒來幾次的另一個原因。尊嚴像是沙漏裡的沙,隨著身體機能的喪失,一點一滴地流光了。被像嬰兒一樣翻弄、擦洗、餵食。我感激他們的照顧,但內心深處那個曾經是大男人的我,卻羞愧得想找個地洞鑽進去。
如果下一次閉上眼就不醒來了,是不是就能保住最後這一點點尊嚴?
可是,就在這時候,門開了。
「阿公!」
是小孫女。她剛放學,背著粉紅色的書包,像一陣春風捲進這個充滿藥水味和老人味的死寂房間。她不嫌棄我身上的味道,趴在床邊,用那雙暖暖的小手握住我冰涼的大手。
「阿公,我今天考了一百分喔!」
那聲音清脆得像是銀鈴。我的心臟猛地跳了一下,那原本微弱的火苗,突然被這股生命力給搧旺了。
不行。還不能走。我還要聽她說說學校的事。我還要看她笑。
加一。我又醒來了一次。這次是為了妳。
第四章:時間的相對論
愛因斯坦說時間是相對的,我在床上徹底領悟了這件事。
痛苦的時候,一分鐘像是一年。半夜痛醒,看著窗外漆黑的天空,聽著時鐘滴答滴答,每一秒都像是拿著刀子在骨頭上刮。我祈求天亮,但黎明總是遲遲不來。
回憶的時候,十年像是一秒。我想起跟阿秀去阿里山看日出,金光乍現的那一刻,我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。那個畫面如此清晰,彷彿就在昨天,但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
我開始混淆了。
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?坐在旁邊的是我兒子,還是我也已經過世的父親?
有時候我醒來,會驚恐地發現自己忘了怎麼呼吸。那一瞬間的窒息感讓我以為大限已到,但隨後肺部又抽搐著吸進一口氣。那一刻的恐懼是真實的,但隨之而來的平靜也是真實的。
我開始跟心裡的恐懼對話。
「你在怕什麼?」我問自己。
「怕被遺忘。」心裡的聲音回答。
「怕沒人記得你曾經來過這個世界,怕你走了之後,地球照樣轉動,兒子照樣上班,孫女照樣長大,彷彿你從未存在過。」
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嗎?一輩子為了家庭、為了社會做牛做馬,最後躺在床上,卻在擔心自己的存在感。
但我轉念一想,看著床頭櫃上那張全家福。那是我七十歲大壽時拍的。照片裡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,兒子像我,孫女像我。我的基因,我的教誨,我做的紅燒肉的味道,其實都留在他們身上了。
就像一顆石頭丟進湖裡,石頭沈下去了,看不見了,但漣漪還在擴散。
我不是消失,我是融化了。融化進他們的生活裡。
第五章:最後的結算
夜深了。
房間裡只剩下那台氧氣機規律的運轉聲,還有牆角小夜燈發出的微弱光芒。兒子在旁邊的摺疊床上睡著了,發出微微的鼾聲。那是讓人安心的聲音。
我感覺身體越來越輕,那種沈重的束縛感正在慢慢解開。
我閉上眼,開始進行最後的盤點。
- 這輩子,沒做過什麼大官,但也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。
- 養大了一兒一女,他們都正正當當做人,這算及格了。
- 對阿秀,我有虧欠,年輕時脾氣不好,常惹她生氣。等我去見她時,得先買束花賠罪。
- 對父母,我盡了孝道。
- 對朋友,我有情有義。
算盤打得差不多了。
我心裡默默數著:
今天醒來了五次。
昨天醒來了六次。
前天是八次。
數字在倒數。這不是悲劇,這是自然的法則。就像太陽下山,就像葉子落下。
突然間,我好像看見了一條河。河水很清澈,閃著銀光。阿秀站在對岸,這次她沒有變成舊外套,她清晰得連眉角的痣都看得見。她向我招手,嘴型說著:「老伴,來啦,水已經燒開了,茶泡好了。」
我感覺到一陣前所未有的睏意。這一次的睡意不同以往,它不帶任何威脅,它是溫暖的、金色的。
心裡的算盤停了。
我想,我不需要再算還能醒來幾次了。
因為這一次,如果是睡著,那就是去見老朋友;如果是醒來,那就是再看一眼親人。無論哪一邊,都是好結局。
我看著天花板那塊水漬,它現在看起來像是一雙翅膀。
嘶...呼...
呼吸聲慢慢變慢,變輕。
兒子,被子蓋好,別著涼了。
孫女,考試不要太緊張,快樂就好。
阿秀,我來了。
我閉上了眼睛。心裡那個計數器,終於歸零,安靜了。
給讀者的話:
如果你讀到了這裡,請放下手機,去抱抱身邊的老人家。他們的沉默裡,藏著一整個宇宙的波濤洶湧。他們每一次的睜眼,都是為了多看你一眼。別讓他們的計算,變成無人知曉的孤獨數學題。
.png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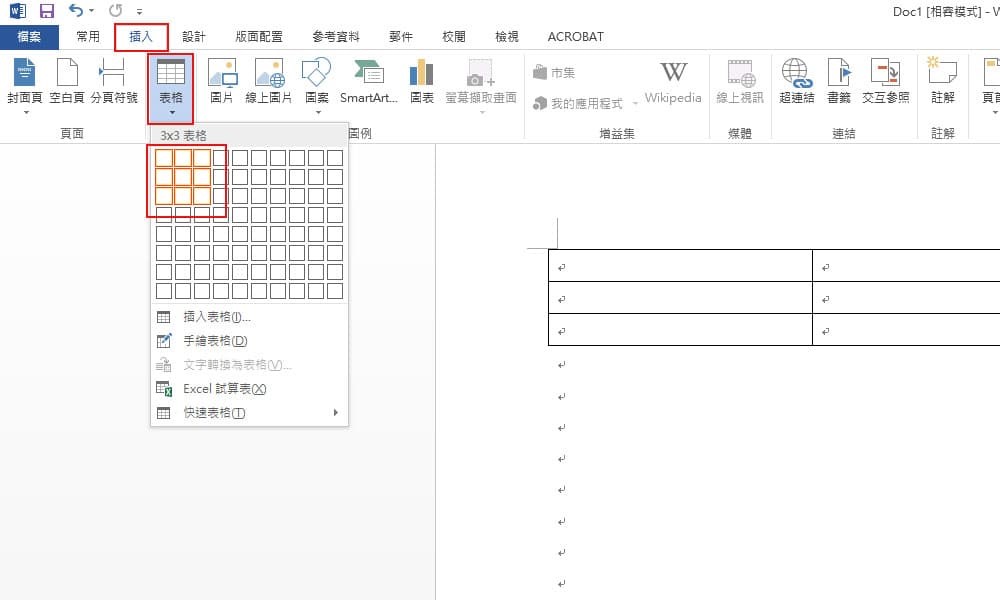

留言
張貼留言